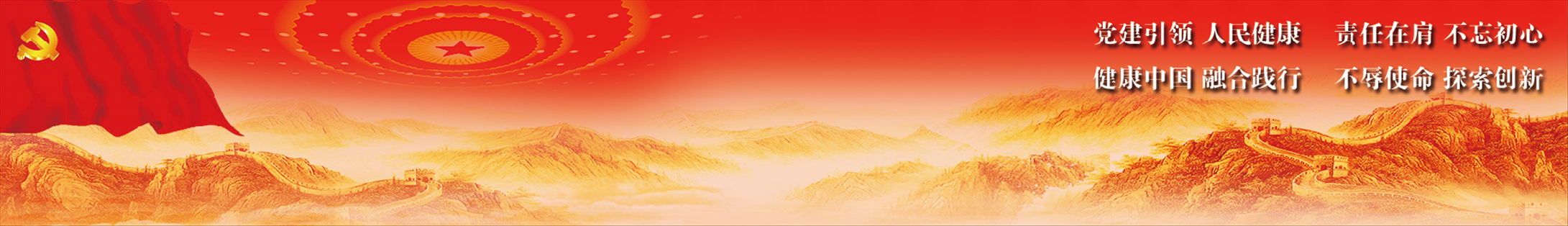一个村医照顾千人,退休金每月只有两三百

文 / 巴九灵
国庆回村一趟,几次路过村卫生所,总是一种可开可不开的景象。
一天晚上7点,门就是关的。后来医生说去过生日了。第二天下午4点,只有两个人,一个是意兴阑珊的医生,一个是呆坐的看门的奶奶,房子里的灯昏昏亮着。

小巴/拍摄
再到晚上6点,只剩下奶奶一人,说医生去吃饭了,要一个小时后才能回。
小时候经常去村卫生所,渐渐也就混熟了。那时房子里总热闹,通明,老医生很有威严,精力旺盛。
长大偶尔去时,也有一些余味,老医生的儿子和儿媳妇忙前忙后,画面颇为和谐。
而如今这番景象,大概可以判断老家的村卫生所是没落了。
村医群像:与时代的进步擦肩而过
翻开卫健委每年都有的统计公报:2017年,乡村医生有90.1万人。2018年,是84.5万人。2019年,是79.2万人。2020年,是74.2万人。每年平均以5万人的数量减少。
2021年,没有再明示乡村医生的数量变动。但有一个数据似乎更赤裸,“持乡村医生证的人员和卫生员”2020年数量是79.6万人,到2021年是69.7万人,相差近10万人。
陕西商洛市某行政村村医李光明,今年马上要40岁了。在他们镇的38个行政村中,40岁左右的村医仍是中坚力量。
李光明一个人“一条枪”管着村卫生所,2000个村民有啥头疼脑热都是他的事。这一干就是二十年,以至于家也牢牢固定在村子里。他中间也有过动摇,特别是有了两个孩子以后。
以往的一幕幕不断浮现他的眼前,迈步飞奔的城镇化把越来越多人带去了城市,他们在那里买了新房、安了家,他们的孩子在那里上了学,硬生生地把他们的人生划出了两条路,别人走的是一条是阳关大道,他自己走的却是一条是崎岖小路。
临近四十岁,他为自己后路考虑的心理更迫切了。
如今,他年收入总数大约在4万元。没有编制(但受镇卫生院管理,有事需请假)。没有主流企事业单位的五险一金,只有一个保险。
如果退休,每月会有两百块钱的退休金,这是身边已退休村医的情况。上有两个老人,下有两个孩子,但他当不了家里的顶梁柱,还得靠老婆外出打工赚钱。
他的爸爸去年做了五个心脏支架,妈妈长期高血压、糖尿病。此外,“今年我丈母娘宫颈癌又花了一大笔钱,弄得人手里没点存货,心就慌了”。
李光明的爷爷曾是县里的医生,曾建议他从医,最终他大专毕业(那时的大专学历未必很差),落得个村医当。如今,他总觉得未达到爷爷的期待。

来源/网络(配图与内容无关)
李光明的尴尬处境不是个例。济南一位四十来岁的女性乡村医生张健,干了十来年,每个月收入2000元。一开口就说,不想干、想改行了。
河北省衡水市高新区苏正办苏义村的村医何文库,42岁,月薪2000元,半年开一次工资。“这编制问题,国家卫健委早就说解决,到现在还没解决呢。”何医生对小巴说。
山东泰安的韩医生,今年57岁,从1986年开始干乡村医生,目前月收入还不到2000元。
黑龙江大庆的毕医生在今年4月退休,从二十多岁开始干,干了有38年,负责1400个人,月薪2000—3000元。每月退休工资是300块。退休后,他也就不被允许行医了。
“要不说乡村医生悲哀。”电话那头叹息道。为补贴家用,毕医生种了不到八亩地,每年多挣个万八千。
从全国看,只有少数经济较发达的地区,村医才有编制和较可观的收入。李光明们的遭遇则更为普遍
村医的消亡重要吗?
有人可能会说,选择权就在他们自己的手里。
有想法、有理想的村医都走了,而李光明之所以还在犹豫,是估摸自己也干不了别的,并且能从这项工作中获得一些成就感。
村里曾有一个老太太有心脏病,一有头疼脑热就容易发病。去大医院一次可能要几千上万元,但在村卫生所只需要四五百块。还有一个老人脑梗、半身不遂,躺了十几年,李光明记得给他打针时,老人指甲缝里头都是泥。

来源/网络(配图与内容无关)
“那些大学生,能吃得了这种苦吗?”他说道。过去镇卫生院曾来过一些中医大学毕业的本科生,但最后都没有留住,待不到半年就走了。平时,乡亲们也会给李光明送点自种的黄瓜、豆角、土豆和红薯,以示感谢。
无论是同行,还是领导也都在说,国家慢慢在重视这一块。前年,省卫健厅一个副主任下来调研时,就跟他们聊了很多奉献。
“不会把你们忘掉的。”对方许诺说。
济南的女乡村医生张健对于外出打工的同乡“有点眼红”,但有时候也自我安慰。
“想想也挺甜蜜的,在家最起码和老人、孩子能在一起。”他们家共八口人,都居住在农村。
但不断严峻的现实情况,冲击着他们的底线。“我奉献可以,但我孩子怎么办?”李光明说。
“孩子考试一塌糊涂,我也管不了。”张健无奈说道。
从2010—2012年左右,单干散布、自负盈亏的村医实际上被政府纳入公共卫生项目,不再允许单干。
村医的收入主体不来自看病、卖药,而是来自财政拨款,工作内容是定期采集村民身体信息以及随访,成果接受上级的严格管理和考核。而后者挤占了村医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。

来源/网络(配图与内容无关)
黑龙江大庆的毕村医说,每个季度都要去随访,测血压、测血糖等,一次要花上十天半月。孕产妇、0~6岁儿童、65岁及以上老年人都得归他管。上班需要录指纹,村卫生所全程接受视频监控。
“针对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冠心病等重点人群的联系电话不能停机,停机就扣分,扣分就扣钱。”山东泰安的韩村医说。
截至2021年底,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.67亿,占总人口的18.9%,其中农村老人占近一半。
公共卫生项目就像一张大网,打捞起了广袤乡村土地上难以采集的老人、幼儿、孕妇的身体状况信息,起到对乡村医疗情况统一管理,提前发现和解决问题的作用。
比如,“2020年老年人体检发现冠心病问题,检查结果和大医院查出来的一样,这才让我村的老百姓竖起大拇指来,说我们的公卫体检太好了。”何文库说。
近三年,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从74元涨到84元。一般是卫生院拿60%,村医拿40%,多劳多得。
而药品则由上级医院或者承包商统一配送,利润空间小,药品少且贵。
至于村医的老本行——看病和卖药被彻底边缘化。
“后来就不太愿意看病了,因为公卫的事务繁忙、药品不便宜,出了问题可能连累到上级部门。”毕医生说。
但是,不论是作为村民就近医疗的必要存在,还是类似有关部门聘请的临时工作人员,村医都承担着关键的作用。
并且,一旦发生公共卫生安全事件,如新冠疫情,村医也被号召战斗在一线。
“2020年大年初一,就接到医院通知需要去高速值勤,自己带着方便面和热水……”何文库说道,尽管他自己也觉得无怨无悔。
“农村的老人也是老人”
结合这样的现实,再看我们的宣传环境。以下是常见的几则官方新闻:
1. 溜索出诊的云南村医,终于不再溜索,当地通了公路。他说:“一辈子当村医,绝不后悔!”
2. 江苏盐城的乡村医生13年资助150名残疾孩子。
3. 四川自贡市的“跛脚”村医,服务村民21年。“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,只要跟黄医生联系,他都会随时过来。”村民说。
村医新闻总是与无私奉献绑在一起。一部分村医的伟大,似乎成了全部村医的行为准则。
而显然这也对更多的广大村医形成了一种道德的宣导甚至绑架,致使村医群体的待遇改善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,甚至对不明就里的局外人造成一种错觉。
老百姓不理解他们,认为他们是国家公务员,有丰厚的待遇。“你们多好啊!开着公务员的工资”“你们都领着国家的工资,都是应该的”——老百姓经常说这些话。但他们很难解释,常无言以对。
村医群体,让小巴联想到疫情期间同样承担一线工作的社区工作者群体,他们和村医类似,收入不高、没有编制,却事实上成为了苦活累活的承担者。
在媒体上,他们也有类似的无私奉献的面孔。可见这是我们的一个“传统”。
而据小巴了解到的情况,立足于城镇社区的社会工作者的岗位或许还有后续的补充,而乡村医生的岗位,则未必后继有人了。

来源/网络(配图与内容无关)
如今各地都在轰轰烈烈展开的定向培养大学生村医的工作,需花钱签约医学生,后者承诺在乡村服务若干年。
但据甘肃省卫健委官网披露,甘肃省2015年至2019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违约者数达251名,从2015年违约5个人飙升到2019年违约85个人。违约者将面临收回培养费、收缴违约金,不诚信行为记入个人档案等措施,但即便如此也挡不住违约形势。
在社交平台,违约和跑路的医学生故事比比皆是。今天的年轻人对于个人利益问题更加敏感,不愿意接受没编制,常被拖欠工资且强度大、环境差的工作。
更何况,要干好公共卫生项目,需要较长期扎根服务村民的耐心,要做到这些,需要李光明、何文库这样十年如一日顽强奋斗的中流砥柱。
何文库说:“最初公卫工作特别头疼,好多老百姓不理解,现在好多了,我没事了就和老百姓拉家常,从中给老百姓宣传咱们公卫的好处……我必须啃下这块骨头,后来全部被我拿下了。”
李光明的方法总结起来是:通过看病跟病人先建立信任关系。如果缺乏这一层关系,病人不可能完全按照医生的想法去做,包括饮食习惯、生活习惯、按时吃药等。即便是一开始跟得上,后期也跟不上。
一位上级委派的扶贫医生曾去到一个病人家里,和病人嘱咐了少抽烟、戒酒、饮食少油等禁忌。病人一开始跟得上,但后期就走偏了,因为他自己也不太懂,结果吃的东西越来越少,导致营养不良。
显然,再高明的医学建议也不能生搬硬套,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一次性解决问题,需要长期细致的随访和医学普及。
但是,他们的待遇如此不堪,难以对年轻一代产生吸引力。

来源/网络(配图与内容无关)
小巴出身农村,清楚知道拥有6亿规模人口的农村的许多东西都在坍塌,无论人口、教育、医疗、商业资源等都止不住流失,这并不足为奇,但村医群体的坍塌却可能是致命的。
因为老人们离不开农村了。李光明最后说:“之前国家说要让全民健康,农村老年人的健康也是这一部分。农村的老人也是老人。”
注:除何文库,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